嘉德殿前
黎嘉德非常喜歡他的中文名字。篤信道教的他相信人生的一切環環相扣,看似巧合的每一個事件都有其目的與因緣。比如說沈次長給他取的名字,黎嘉德,便隱含了許多與他人生目的相關的契機。黎嘉德,可以說是黎明的嘉賓。易經八卦,元亨利貞中的易乾卦,也有「亨者嘉人會也」之說,好人聚集自然亨通,象徵了他的命運。
他對中國古籍深入爬梳,涉獵之廣,令許多中國人汗顏。再以黎嘉德這個名字為例,他盛讚中國文字的美好,引用書經中帝堯禪讓於舜,謂之「乃懋乃德,嘉乃丕績」,嘉德嘉德,呼之欲出。
雖然已一別四十多年,黎嘉德對於他第一次來台的印象依然歷歷如繪。一九五八年元月,他由母親陪同前來,飛抵台灣的那天,台北下著濛濛細雨,正是典型的東北季風氣候。當時的台北多是小小庭院、花木扶疏的日本式房子,街道也窄,延平北路、中山北路、萬華、羅斯福路,在雨中漫步,充滿了詩意。
當時,一個來自那麼遙遠國度的青少年對中國文化如此熱愛,媒體大幅報導,在台灣社會引起了相當的轟動。他也被引見給許多政要名流,而他對中國文化素養深厚的監察院長于右任、考試院長賈景德、教育部長張其昀、畫家馬壽華等印象最為深刻,尤其是于右老、賈景德、馬壽華都是書法大家,更讓他對中國書法心生嚮往,奠定了日後走上漢學研究的人生方向。
黎嘉德在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得到博士學位,師從專研宋代大畫家米芾的二十世紀歐洲漢學大師Nicole Vandier-Nicolas ,受其影響深遠。他的博士論文主題是以狂草傳世的懷素,其中以中國書法的演變為經,尤重篆書的變化,而他最愛的是漢喜平石經碑的八分書,便由篆書演變而來,所謂「八分取二分」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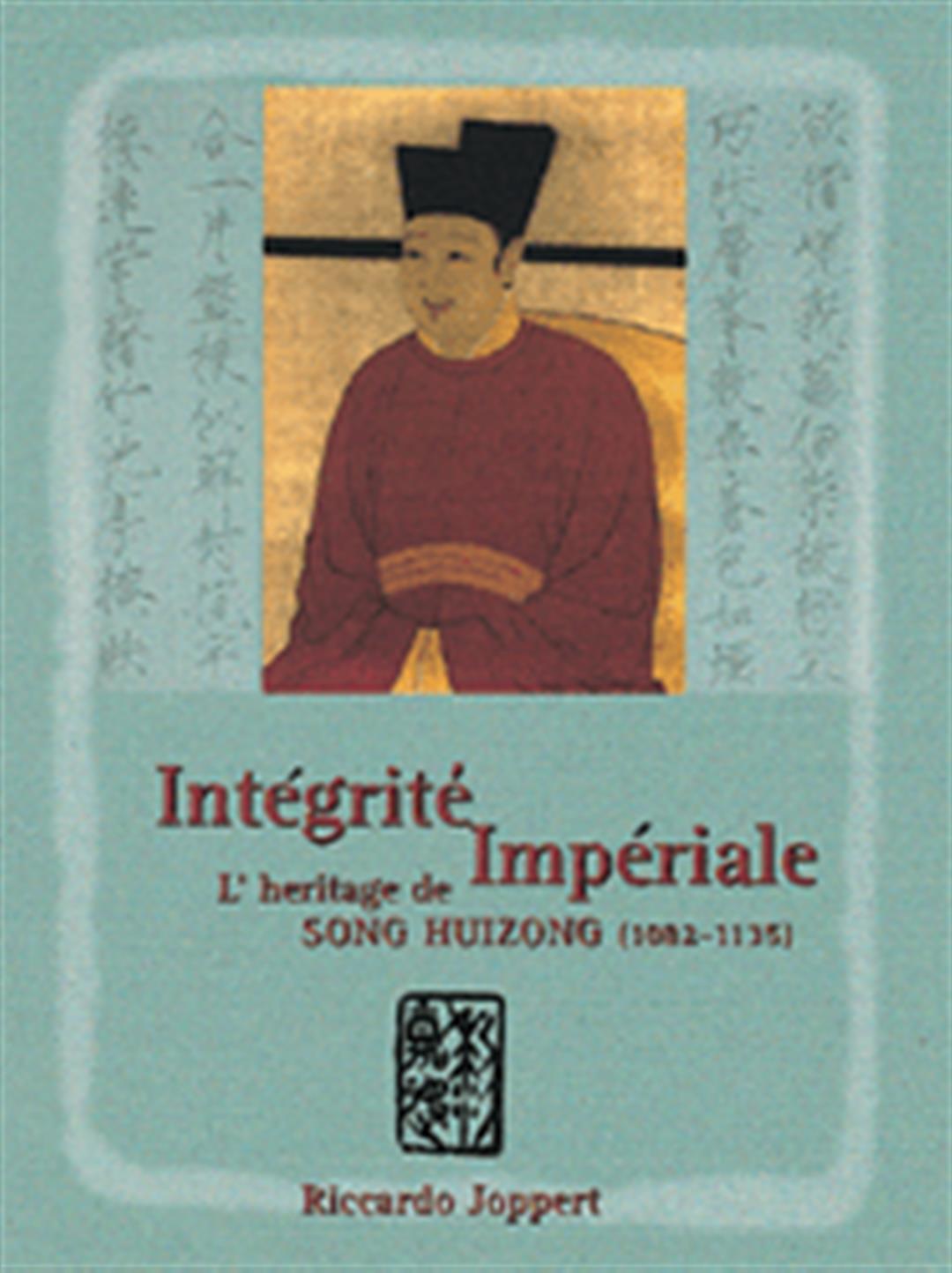
今年三月,黎嘉德縱論宋徽宗對中國文化貢獻與影響的《帝國的情操:宋徽宗(1082-1135)》在巴黎發表,為自故宮《帝國的瑰寶》展後的宋徽宗熱更添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