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學風
高閱讀門檻的台灣純文學和文化著作,在大陸市場上需要細火慢燉,但出書卻往往如投石於海,能掀起些許討論就不錯了,由於難有廣大銷量,兩岸出版社合作出版這類書籍也較少;現實如此,因此近兩年在大陸掀起熱潮的台灣書籍主要是勵志書和都市文學兩類,其中又以蔡智恆、王文華與幾米等人領軍的「都市文學」最受矚目,一本書銷量超過二十萬冊是基本數目。
蔡智恆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在二○○○年時,挾著網路文學熱潮走紅大陸,也成為紅色出版社所屬城邦集團到大陸的敲門磚。這幾年來,與新浪網運用聯合造勢、辦簽名會、發消息給媒體、作品改編成舞台劇等行銷手法,已成為網路文學、甚至是都市文學作品在大陸發跡的固定模式。
幾米和王文華則被視為大陸都市消費習慣僅離台灣一步之遙的象徵。
二○○○年時,幾米的繪本曾以《世界繪本大師系列》的方式在大陸發行,但連首刷五千本都賣不掉,讓大陸出版業者十分遲疑,認為大陸市場成熟度尚不到接受精緻圖文書的水平,但民間書商北京正源圖書公司的圖書策劃人王冬力排眾議,認為書的印刷與質感若能做到和台灣一樣,要熱賣絕對沒問題。果不其然,幾米一炮而紅。
「幾米有現代感十足的畫風,故事又兼具中國式的委婉、細膩,這剛好搭上大陸新興『小資』階級的情感消費風潮,而大大走紅,」王冬說,現在大陸青少年間有一種說法:「要談戀愛,得先看幾米。」幾米越過海峽後,居然成為戀愛教主。
王冬表示,流行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但選書時仍要符合好看、切中市場品味與選書人自己品味的原則。她舉例,台灣作家吳若權《站在有光的地方》等三本書出版時,雖然碰上SARS風暴,沒做什麼宣傳,但仍有不錯成績,吳若權已排定十一月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辦簽名會,是在大陸剛剛升起的新明星。
另外,作家也要選對適合的出版社,才能有正面加分的作用。
北京晚報出版線記者孫小寧表示,北京是大陸出版中心,此間的媒體書評也能在全國起「策動效果」,照理說,出書的首選之地應該在北京,但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選定由出版《我為歌狂》、帶動「青春文學」熱潮的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擔綱,上海人特別懂得操作流行時尚議題,剛好符合《蛋白質女孩》的風格,新書上市一個月,就狂銷十五萬本,作者與出版社都獲得「加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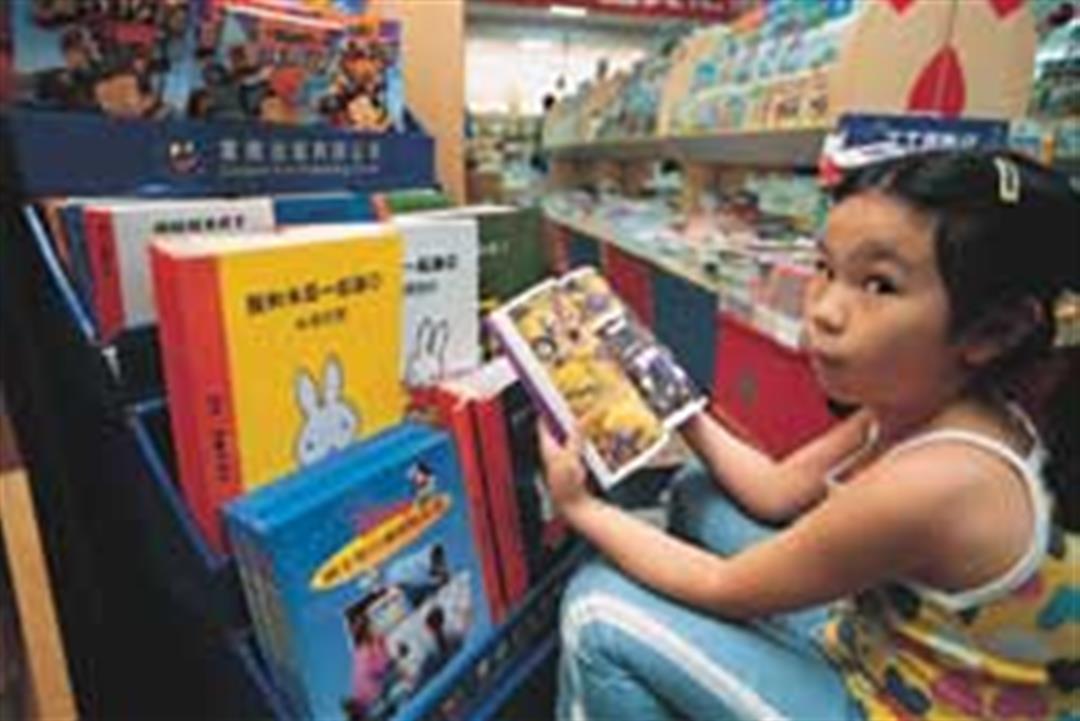
(右)從文學、生活、科技、語言,到童書,大陸城市地區圖書消費力漸強,每個領域在出版業者看來,都隱含無限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