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選擇的權利
她不諱言,這些年有幾次機會回印尼,其實更像回一個度假村:殷勤的母系親人、鄉下老宅與郊區購物中心,還有熟悉的客家聲腔,問她「看見了什麼?」,她笑了笑:「還真沒看見什麼!」。就跟你我記憶中的返鄉一樣,幾分新鮮、幾分尷尬,叫不完的叔伯阿姨與鄉村風光,就是沒那些大家以為的「二代血淚尋根記」。
當然,身為新二代,陳又津的書寫免不了會面對母國或家鄉,好在對她而言,這不過是轉身之間的事情,而非失根、迷途;她甚至拋出一個問題:什麼是新二代?「說不定根本沒有新二代啊!」她說。每個人都如此獨一無二,誰不是新的一代?那就邊走邊找吧,一邊漫遊,一邊尋找自己的座標。
陳又津在自己的文字裡悠然自得,更像散步、玩耍,所以顯得更有餘裕。她承認自己是幸運的,那些標籤不曾傷害她,但也許傷害過其他孩子,她也希望政府打造一個友善的環境,而非是血緣上的友善。
血緣上的強制友善,是因為你的身分,給予特別的優惠,反而令人沉重;而環境的友善,就像是菜單上並列四種語言,台灣人、印尼人、菲律賓人、柬埔寨人同時都看懂了,這過程不需要一點聲音,每個人自然能溫柔會心。
陳又津表示,新二代不是非要政府做些什麼,而是希望能保留選擇的權利,生命是溫熱的,不是一份專案,需要更多自由,去找尋自己的出口。
如果新二代的旅程還在繼續,那麼,「準」台北人會有「跨過去」的那一天嗎?「這可能是一場積分賽吧,永遠都在準備跨越,但愈是意識到自己在準備區,就會一直停留在那一區。」陳又津如是說。
少女繼續在城市漫遊,看似漫不經心,其實步步縝密。正如細川匯聚成河,每一個細碎的字句都指向情感記憶;亦如大橋連結台北與三重兩端,只要連上了,就能溝通。準確或者不準確無從定義,但至少願意傾聽,已經足夠。

陳又津開朗的性格與笑聲,更趨近於少年的爽朗明亮, 同時也反映在作品中。(陳又津提供)

少女陳又津在台北漫遊,橋的此端與彼端, 但不定義,只傾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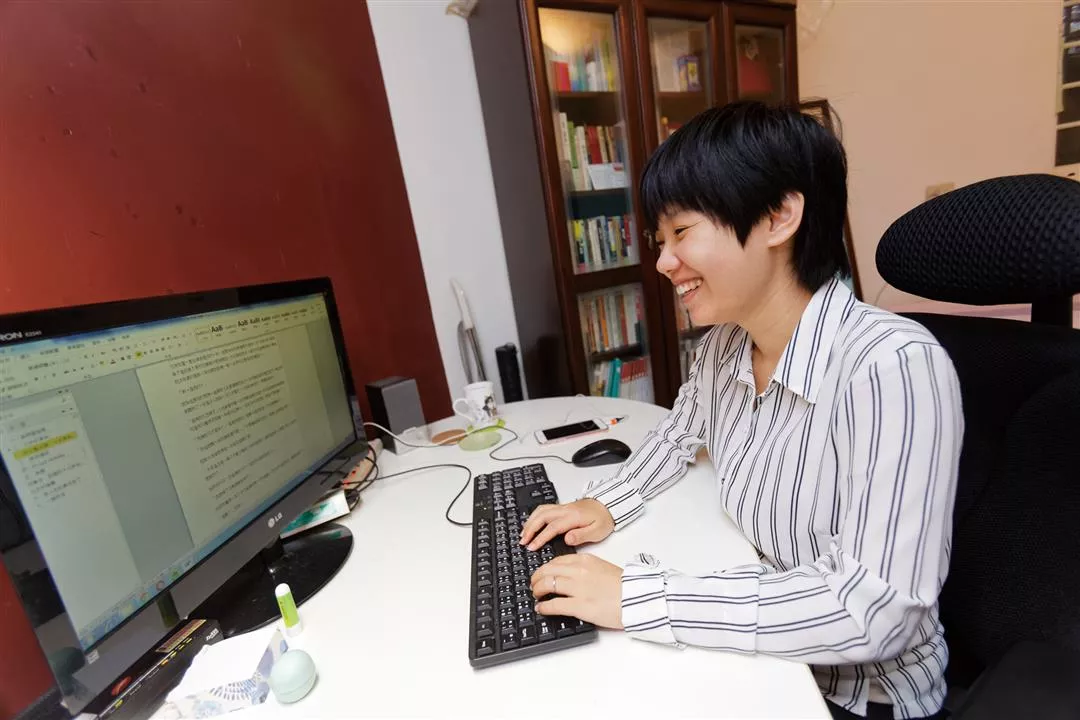
陳又津在自己的文字裡悠然自得,更像散步、玩耍, 所以顯得更有餘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