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旅遊願景
未來,碧候社區計畫發展生態旅遊,運用北溪豐富的自然資源,來吸引遊客。林金助表示,地方上有些人士主張發展北溪溫泉,但鑒於許多溫泉區的開發,常因財團介入,原住民無法主導,不但未能獲益,反而破壞了他們生活賴以憑藉的自然環境。他希望未來的生態旅遊能以環保教育為訴求,將祖先與大自然共處的智慧流傳下來。
沿著南澳北溪一路而上,溪水潺潺、巨石嶙峋、林木茂密,沿路有許多瀑布奇景、野溪溫泉。據當地居民表示,北溪因為生態系統完整,擁有豐富的鳥類、哺乳類、昆蟲、魚類等資源,越往上游,景色越是奇麗。
「可惜,前幾年因為上游開採石灰,受到污染,」碧候社區發展協會新任總幹事蔡世明指著岩石下沉積的灰色泥巴說,以前可以釣到十五公分長的苦花魚,現在都沒了,如今雖然上游已經停止開採,但北溪要恢復原來的面貌,還要一段時間。
蔡世明指出,目前社區想推廣的生態之旅,主要是北溪的支流「那命」,「因為那裡沒有污染,溪水中有好多毛蟹、苦花魚、香魚、溪哥、鰻魚......,一路都還可以看到山豬、山羌、山羊......,」蔡世明談起「那命」的溯溪經驗,十分興奮。
至於要如何推動?碧候目前還處於規劃「願景」的階段,包括推動民宿、設立多功能文物館(含生態旅遊服務)、培養生態解說員等。
雖然看來前路迢迢,林金助仍然樂觀以對,尤其去年接連獲得全縣及全國社區評鑑優等,讓他覺得社區已逐漸步上軌道。
「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對社區營造這麼投入,」每天清晨五點上山照顧菜園、白天上班,晚上和假日則奔波於社區及外地開會的林金助說,有次看到一個年輕人扛著一個酒醉的中年男子回家,「我們原住民不會放棄別人,這就是文化傳承,希望這樣的精神,能讓碧候凝聚起來。」

碧候的「比亞豪」舞蹈團由社區媽媽組成,近年小有名氣。既能為社區爭光,又可以運動聯誼,她們跳得可起勁呢!

碧候編織班學會織布後,還設計了許多現代生活用品,如手提包、手機包、桌巾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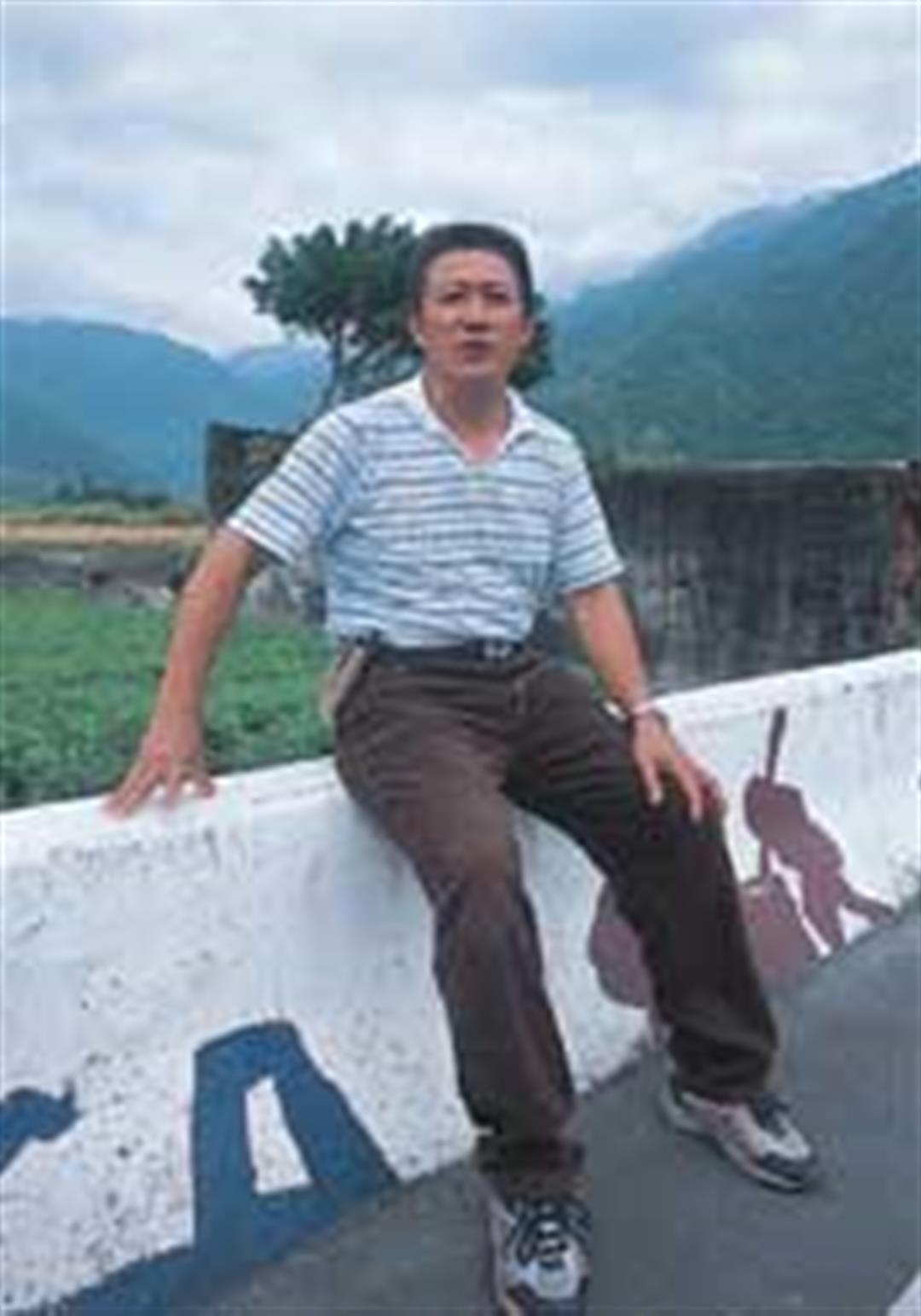
五年來林金助「校長兼撞鐘」地推動碧候社區的運轉,辛苦備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