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祇有像我這種老鼠一樣的人才會了解:那樣一個世界正是我們失落自己的倒影。
《城邦暴力團》是夙有「文學頑童」雅號的名作家張大春最新力作。挾著穎異的天資、文字的高敏感度,以及他博識多聞的學問功力,張大春宛如變戲法般地「變」出了上起清初康熙、乾隆時的「江南八大俠」,中歷國府時期的「清洪幫」,下迄當今社會的「竹聯幫」之「黑道譜系」;箇中引經據史,旁及醫藥術數、武功源流的考鏡,再加上若干「嚮壁虛構」、「存心作偽」的「自鑄偉詞」,原來只具有符號性質的文字,在他筆下雲翻雨覆,剎那間變幻出不可思議的華彩;配合著他刻意營造出的錯雜纏結之敘事時空、真實與虛構混揉的「自我介入」,交織出一片魔幻詭異的色調,似真非真,如假非假,很成功地引領讀者步入他蓄意塑構的「圈套」與「騙局」之中。
說「圈套」、「騙局」,其實沒有誣蔑張大春,不但其「自成一家之言」的所謂「黑道譜系」,是個騙局;就是他自言此書是企圖突破已經「一洗凡馬萬古空」的金庸武俠小說「黑洞」,自定其位為「武俠小說」的說法,也是個「圈套」;更有甚者,當今的社會(城邦)──包涵了政治、文化、經濟各層面,無非也是個讓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大圈套」。身在社會中的所有人,當局而迷,不明究裡,唯有「鼠眉鼠目」的張大春之流,才能洞察此一「圈套」的底細。可是,老鼠是見不得光的,真相的光芒刺眼,於是乎只能侷促斗室,要不就逃逃逃逃逃逃逃……
七本書的奧秘
這個「圈套」的一系列精心設計,是由七本書開始的。這七本書,來歷十分清楚,作者、書名、出版社、總經銷,一一載明,而出版期則「剛好」與敘述者在「三民」書局閱讀的順序相符,在第三冊頁85,張大春如是寫著:
《食德與畫品》魏誼正54、11
《神醫妙畫方鳳梧》萬硯方54、12(上市時作者已歿)
《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汪勳如55、1
《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陳秀美(疑為錢靜農化名)56、1
《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陶帶文(即李綬武之化名)61、1
《七海驚雷》飄花令主66、1
《奇門遁甲術概要》趙太初66、7
這七本書,「當然」是虛構的,但是,張大春卻「請」出了已故的歷史小說巨擘高陽來「背書」,眉批夾注的評點、闡發不說,更語重心長「點明」其間的「可能奧秘」。高陽在歷史研究上的造詣,向來是有口皆碑,恭請前輩為此虛構的「秘笈」佐證,毫無疑問地,是有意「除虛就實」,增添《城邦暴力團》的可信度。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張大春企圖擷取金庸、古龍兩大家優長,而加以「轉精」的用心。
金庸假歷史為鋪墊的武俠創作,早在讀者口耳喧騰中,樹立了典範。張大春向以金庸為「武俠黑洞」,欲極力擺脫的雄心,自是督促他創寫《城邦暴力團》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張大春深厚的國學根柢,逕取史實,「模仿」金庸「亦虛亦實」、「化虛為實」的手法,以慷慨壯烈的歷史背景為豪傑英雄樹立形象,自亦可行(當然,成就如何,尚待評論,《武林外史》即為一例);但朝華已披,夕秀難振,踵襲前賢,畢竟非當行本色,料想他也是萬萬不可能再為的了。翻空出奇,借金庸蹊徑,而別走途轍,當是《城邦暴力團》的創作路線。金庸的特色在依附歷史,千變萬化中,自有其規律可循;《城邦暴力團》則自創歷史,表面上黏附野史奇譚,而終究一派荒唐之言。在這裡,徐克導演、林志明編劇的電影《蝶變》,起了重要的影響。
從《食德與畫品》到《奇門遁甲術概要》,張大春巧妙地運用了他豐贍的歷史知識,擷取信史、野史、傳說、小說中的散片,規模宏偉地構築了他的「江湖史」,從清初的「江南八俠」到當今黑道的「竹聯幫」,居然同氣連枝式的貫串了起來,這是多聳動聽聞的「歷史」!偏偏張大春就有這種本事,我想,學術背景是他的得力處,因此「變造」得相當高明,幾乎可以「亂真」(說來好笑,學術研究與考證,恐怕也少不了類似這種的蓄意變造)。這七本書,就是記載這段虛構的「江湖史」的「偽書」──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武林秘笈」。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蝶變》中的《紅葉手札》。
《蝶變》是一部在七○年代相當重要的武俠電影,開啟了徐克新銳的導演風格。此劇是由林志明編寫的,很多評論者從此劇中窺見了《蝶變》模擬西方電影技巧的關竅,卻少有人論及此劇與已故武俠鬼才古龍小說的神似。細心的讀者很容易發現,古龍的小說,有其自成一套的「江湖史」,從《武林外史》中的沈浪、王憐花,到《多情劍客無情劍》的李尋歡、阿飛,到《邊城浪子》、《九月鷹飛》中傅紅雪、葉開,以及隨處皆不忘提點的「百曉生兵器譜」,古龍的「江湖史意識」,是十分明晰的。我們不敢確定,徐克與林志明是否曾受到古龍的影響(儘管在我看來,是肯定的),但《蝶變》中的方紅葉,覶縷記載武林秘辛,手撰《紅葉手札》,就是一部具體而微的「江湖史」,與古龍正有異曲同工之妙。
無論是《蝶變》或古龍,江湖史的締設,都是純粹虛構的,目的在於凸顯另一個異於尋常知聞的世界,此一世界,是獨立而自足的,《蝶變》的七十二路烽煙,無須任何歷史的佐證;古龍自沈浪而下的譜系,也無須傳記譜牒的支持;不必以真濟假,以假亂真,一個是新派武俠的「電影」,一個是新派武俠的「小說」,光是精采淋漓的畫面、影像,曲折離奇的情節、人物,就夠讀者(觀眾)陶醉沉迷於其中了。這個「江湖史」,早已經文類慣例賦予了約定俗成的意涵,虛構(假),就是最大的共識。
《城邦暴力團》顯然有取於其「假」,但卻蓄意破壞此一共識,他要讀者深深陷入透過學術考證、史學知識營構出來的「假」中,信以為真。因為這個「假」的建構,非常弔詭的,居然是一連串「真實」的散片所組織起來的。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圈套,一個騙局。
然則,張大春的意圖何在呢?「鼠眉鼠目」的他,其實窺見了當前社會中一隅的實情:「江湖」真的是無所不在的。然後,他揶揄、諷刺、批判,並化為耿耿的隱憂。
「鼠國」中的陰影 ──俠以武犯禁
張大春自我調侃是隻「老鼠」,其實用意在強調他的「鼠眼」中所窺伺到的「鼠國世界」。老鼠向來與人類並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倏而滅、倏而生」,「鼠國─竹林市」則是「一座看不見的城市」(冊一,頁26)。其實,「鼠國」就是一般所稱的「江湖」,「老鼠」就是「江湖人物」。
在傳統武俠小說中,「江湖」是英風颯爽、嶔崎磊落的「俠客」,行俠仗義、快意恩仇的舞臺;儘管其間正邪善惡,淆然難辨,但一往無前之氣、大開大闔之風,還是清晰可見,與「老鼠」之畏首畏尾、瞻前顧後,大相徑庭。《城邦暴力團》以老鼠隱喻江湖人物,一時之間,英氣消磨盡淨,實際上導因於「俠客」悲情的宿命。對此,張大春無疑有深刻的理解。
自《韓非子》排擠「五蠹」,宣稱「俠以武犯禁」以來,雖經司馬遷在同情的了解下,賦予了道德上的意義;但在傳統的專制政體中,俠客,尤其是擁有武勇,甚至武力的武裝團體,向來受到深刻的猜忌,從秦朝開始,我們就看到歷史如何以強制、壓抑的手段,播弄著號稱為「俠」的一群人物。「俠客」是歷史上的實存人物,可他們不像武俠小說中那麼風光;風光的俠客,通常都變節成俠客的劊子手,漢高祖、明太祖的前例可以為鑑。這本是意料中事,俠客是「國士」,誠如蘇東坡〈養士論〉所論,是有心於權力鬥爭者最佳的前鋒,因此不得不「養」;而俠客一旦受「養」,介入權力過深,又恐其「養虎貽患」,是又不得不壓制。俠客,流轉在養與壓制之間,注定是悲劇人物,《水滸傳》梁山群雄的遭際,就是一種典型。俠客的真實歷史,就是這樣一路巔簸寫下的──伴隨著的是一片巨大的陰影。
黑金亂俠道
在此,《城邦暴力團》頗具歷史的洞識,擺脫了武俠小說中,俠客「事了拂衣去,不留身與名」的坦蕩,而直指俠客醉心於名與利的實質。俠客欲烈烈轟轟、建樹功業,是求「名」;慷慨赴難、仗義輸財,無「利」更不可能。因此,現實中的「俠客」,鑄幣掘塚,甚而以企業化經營圖利;或者勾結牽連,以身從政,是自古皆然的,「黑金」可謂是歷史悠久的俠客行當,最不濟的俠客,才會去打家劫舍。說穿了,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是被過度美化了的「超現實人物」。真實的,無所不在的俠客,儘管的確屬「國士」之流,卻在名韁利鎖中,墮落為孳孳為利、汲汲求名的「黑道」。
為求名與利,現實的俠客,介入經濟與政治之深,在張大春筆下,有相當程度的披露,尤其在政治上,陰謀迭現,更令人毛骨悚然:如新生戲院的大火、陸運通的飛機失事、洪波自殺、軍統局……等等,都是俠客在幕後操控(或受操控)。顯然地,如此披露的用意,當是在譏刺目前甚囂塵上的「黑金掛鉤」、「黑道治國」。從這點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張大春的筆鋒,是銳利而深刻的。
《城邦暴力團》的江湖史,縱越了三百多年,從前清康熙到當今社會,其間自然有其歷史的演變。在此,張大春難免具有「貴古賤今」的觀點,從天地會、江南八俠而下,似乎越具「古味」的俠客,行事越有「古風」,而每下愈況,到民國以來,就越發不堪聞問了。這關鍵何在呢?俠客理想性的喪失、文化素養的闕如、價值觀的向下沉淪,有以致之。這點,我們從張大春的江湖演變史中,是可以對照出來的。
所以張大春說:
那樣一個世界正是我們失落自己的倒影。
失落,其實正是墮落。
p.116
書名:城邦暴力團(全四冊)
售價:每冊200元
出版:時報出版

書名:城邦暴力團(全四冊) 售價:每冊200元 出版:時報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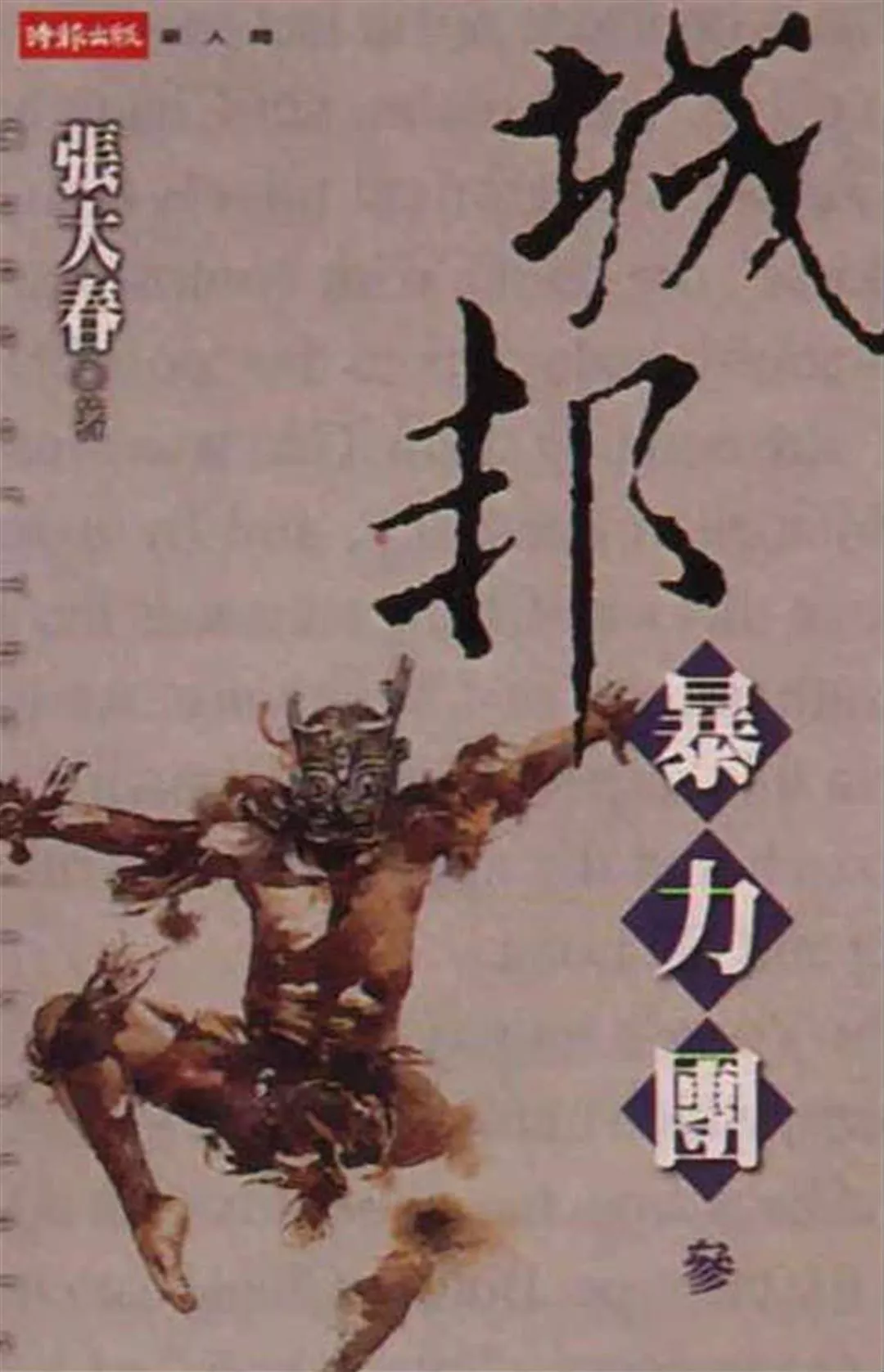
書名:城邦暴力團(全四冊) 售價:每冊200元 出版:時報出版。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