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曾對英國四所著名大學作了這樣的比較:
在牛津,人們會問:“What do you think?”(牛津思想創見)
在劍橋,人們注重的是:“What do you know?”(劍橋認知真理)
在倫敦大學,人們關心:“What do you ‘not know’?”(倫大求知解惑)
至於愛丁堡大學則人人遵循:“What does the professor say?”(愛丁堡承循師訓)
儘管另外三校群起抗議,牛津人可是覺得「深合吾意」呢!
攻讀政治哲學的人,不能不懂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念現代文學的人,不能不看艾略特的「荒原」;湯恩比的「歷史研究」對全世界文明做了綜觀性整理;而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則左右了近代經濟的發展……
這些學者儘管研究領域各異,時間分隔數百年,但是世界學術的「聖城」之一——牛津,卻是他們共同的交會點。
原來,牛津名震士林,是因為擁有這些傑出學者?
「牛津本就為傑出人才而存在:傑出是『當然』,無須誇示」,出過難以數計的諾貝爾獎得主、「傲」氣十足的牛津人如是說。
英國佬講究文化傳承(Heritage),而學術成就,不過是牛津人引以自傲的Heritage中的一部分。牛津無出其右的制度、學風、歷史淵源、校區環境……,才是愈磨愈亮的「鎮校之寶」;就連「宿敵」(Rival School)——劍橋,也只能在「牛劍雙璧」(Oxbridge)中屈居老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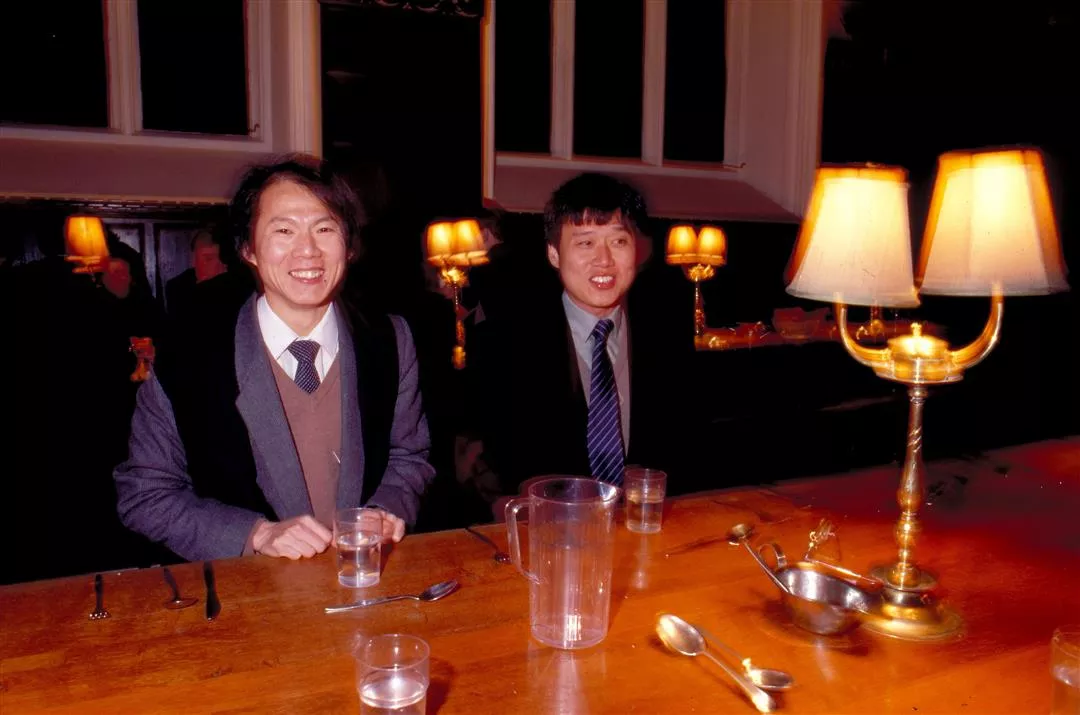
大學與市民之戰
牛津是英國最古老的大學。西元十二世紀初,所謂「大學」(學者聚集、潛修學問,並頒訂學位之場所)的架構在歐陸萌生,英國有不少學者學生,前往當時的法國巴黎大學講道、受業。沒想到一一六七年,亨利二世和法國交惡,他在盛怒之下,召回所有海外英國學者。而在倫敦西北方,已建城近三百年且人文薈萃的牛津市便雀屏中選,取而代之,依著歐陸大學的理念慢慢發展成英國學者聚集之地。
起初,要讓「大學」這個新興產物擠進城市,可也有段痛苦歷程。
一向清規嚴謹的中世紀城鎮,驟然湧入數量眾多、桀驁難馴的年輕人,就「好比蠻族入侵」,當地居民的不安與懷疑可以想見。歷史上幾度有名的「市民與大學之戰」,導火線通常都是學生酗酒鬧事。其中最慘烈的一三五四年「大屠殺」中,數以百計的學者學生被亂箭射殺,學堂也被劫掠一空,直到校長突圍稟告英皇亨利三世,才算把市民鎮壓下去。這一段世仇,還是以牛津市民連續繳付大學五百年罰金落幕的呢!
逐漸地,三面環河、地勢險阻的牛津,不僅成為英國學術重鎮,她的歷史也和政教權勢密不可分。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中,不少新教主教在著名的牛津大街(Broad Street)上被焚殉道;十七世紀英國內戰,牛津更成為查理一世「騎士黨」的皇都所在,整座城頓成軍事要塞。當然,查理一世兵敗處死,牛津也難逃牽連……

建築反映歷史痕跡
「牛津的歷史就是一部英國史,西方文化藝術的每一次思潮,都可以在牛津找到一些痕跡」,「牛津手冊」上開宗明義,傲然定論。
最能直接反映歷史、文化傳承的,自然首推建築。牛津建築風格多變,而無數高聳的大小尖塔,最令人印象深刻。大詩人馬修阿諾的名句:「那甜蜜的都城,那無數如夢般的尖塔!」正是牛津的絕佳寫照。
建於一六六三年的薛爾頓劇場(the Sheldonian theatre),是牛津的「精神象徵」。特異的D型建築,模仿古羅馬劇場;屋頂的壁畫「信(宗教)、美(藝術)、真(科學)與嫉恨邪惡之戰」,畫風雄渾,直追米開朗基羅。每年新生入學、畢業生離校,都在此地舉行典禮,牛津家長們也總要和建築四周的「帝王頭」雕像合照幾張,藉以驕示親友。
牛津的總圖書館——波德林圖書館(the Bodlein Library)則可溯源至亨利五世時代的漢弗雷公爵(Duke Humfrey),他將古典人文科目(哲學、文學等)引進牛津,並捐贈書籍文獻,為牛津學術開了一條新路。直到如今,任何一本在英國出版的新書,都自動寄贈一本來此,波德林圖書館的權威地位,也就不難想見了。

菁華盡藏「學院」中
牛津素以「學院制」聞名,但是此地的「學院」卻大不同於一般大學通用的「工學院」、「文學院」等分法,稱它們為「書院」或許更容易反映其傳統精神。
「三一學院」、「萬靈學院」、「基督聖體學院」、「聖約翰學院」……,一個個都充滿宗教意味——可別誤以為它們是「神學院」,這只是因為西方早期「神本」思想,奉神學為一切學問之根源;而捐建學院的,又多半是有權有錢的教會。時至今日,牛津擁有卅五個風格各異、富儉不均、完全獨立自主的學院,是牛津的主導力量。
在「大學」草創的初期,「學院」就已存在。西元一二四九年,只有四位教師的「大學學院」建立時,「牛津大學」還只是個混沌未明的概念。一些知名的學院,仰仗著捐建者的雄厚財力,營運狀況也較「大學」本身寬裕。而對牛津人來說,「大學」虛有架構,「學院」才是實體,也難怪牛津人的「學院意識」普遍高過「學校意識」了。
畢業於牛津,研究英國高等教育制度的楊瑩解釋說:大學主管學生入學註冊、學期大考、學位頒授等事項;而負責教學授課的,則是大學直轄的各「學部」(相當於「文學院」、「理學院」等)。表面上,大學的權限不小,但其實,大學中絕大部分的行政人員、教師、學生,仍都另外歸屬於某一個學院,這也就是牛津人所謂的「雙重身分」、「雙重忠誠」。

不一樣的「學生宿舍」
換句話說,牛津人不僅有註冊入學的「學部」、「學系」,另外還有自己所屬的「學院」。去「學部」上課,回「學院」生活;「教」、「管」均在師長嚴密呵護中。
那麼,赫赫有名的各「學院」,說穿了不過就是「學生宿舍」?
想要解答這個疑問,必先身臨其境。真正進入學院,才不禁驚嘆折服:這樣的清幽洞天,這樣的薰冶錘鍊,牛津之所以為牛津,而尋幽訪勝之所以必要,都良有以也。
就讀工程學部,住在新學院(New College)的李惠凡,她就有幸有這種經驗:行經「嘆息橋」,穿過一條古靜小巷,推開一座雕花木門,入眼的是草碧花繁的中庭,以及肅穆典麗的四合院。歌聲弦樂,處處可聞;院長、院士、導師、行政人員……都和學生們共食共宿,好一個溫馨的家園。
學院有自己的教堂,莊嚴的管風琴,伴隨著聖詠講道,在主日清晨定時響起。學院內修道寺的迴廊石磚上,刻著先哲前賢的名句嘉言,漫步其間,恍如與古人神交;「靈感來自天啟」,正是許多牛津人共有的經驗。飽藏各類書卷的學院圖書館,經常通宵開放,深夜寒窗苦讀,臨時想到一本參考書,只需簽個名就可借閱,「學院藉著賦予學生完全的信賴,來培養榮譽感和責任心。」攻讀工程博士的蔡明琪尤其佩服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育精神。
此外,學院雖不開課,卻有各式各樣的演講,聘請遠近一流的學者前來開講。今天法學、明天藝術、後天醫學……,林林總總,只要肯花時間、花心思,大學三年,是儘夠滿載而歸的。

生活優渥,有貴族遺風
宗教、藝術,撫平遊子的心緒;豐美的學術環境,隨時誘發創見;而生活起居方面,學院更是無微不至。
每天早晨,學院中的清潔工會為每一位學生換洗床單、清理房間;學院運動場的管理員,會義務為學生舉辦的各種友誼賽備置茶水;在食堂中進正式餐(formal dinner)時,但見服務生川流不息;而在學院自設的酒吧中,則有各色美酒,低價供應學生暢飲解憂。
「在這裡,龐大的編制(Full Staff)和完善的設施,都只為照料區區三、四百名學院學生的生活起居。這種昂貴的教育成本,若沒有貴族傳統為背景,實在很難想像!」一年不過繳一千多英鎊「學院費」,李惠凡常驚羨於這種「豪華」的生活方式。
牛津規定,凡是新生,必須在「學院」中住宿,以免因人地生疏而有不必要的適應困難。通常大學部學生可住滿二至三年,而研究生則住滿一年後須遷走,把機會讓給後人。各學院名額少至一百、多至五百,額滿即不再收。這也意味著:「牛津若不能保證給你最好的學習環境,就不會貿貿然收你」,在聖安東尼學院就讀的黃克武說。

培養健全的社會人格
不止如此,在英國傳統信念「大學功能不在職業教育,而在養成人格」的影響下,「學院」的確是用心培養健全的社會「人」。
蔡明琪舉一個例子:學院食堂每天晚上六點供應便餐外,七點另有「正式餐」,學生可視情況登記參加。進餐時,每位學生服裝正式,外罩黑袍魚貫進入。七點十五分鈴聲一響,教授們則由內室進入,在高桌(high table)落座,準時開飯。
學生餐是一壺水、一籃麵包、一碟炸馬鈴薯、一碟水煮青菜、加上兩片煮羊肉——雖然簡單,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餐飯與同學交談下來,精神收穫甚於物質收穫。遇有特殊日子,學院還會準備特別的「宴客餐」(special guest dinner),讓學生自由邀請朋友參加,藉此培養社交能力。
英國人重社交,禮儀口才都列為才學評鑑的一部分。別的不說,學院院士們早在正式餐入席前,便齊聚一堂,暢言讜論;學生吃完離席時,「高桌」上的正餐(main dish)還未開始;餐後又群往酒吧小憩。這漫長兩三小時,可不是一般人胡扯亂蓋所能比擬。無怪乎蔡明琪有感而發:「真不知道這些院士們每上『高桌』吃頓飯,要先讀多少書!」

導師見面禮——信心危機
「導師制」則是學院另一項引以為傲的傳統。它最早的起源,是貴冑世家不放心子弟離家就學,因此特別由父親挑選一位學院院士做為監護人,全權管教。演變至今,貴族傳統雖已式微,這種制度仍然嘉惠著無數學子。
「導師」等於是學院為學生聘的「家庭老師」,專門解答課堂上未解的疑惑、督勉學生用功。導師權責還不僅於此:感情挫折、身體不適、社交障礙,乃至於遊子思鄉……凡是足以影響學子求知情緒的,都在導師協助範圍內。
不過新生和導師第一次「晤談」,往往會經歷信心危機。導師輕描淡寫一句話:「最近讀了那些書?」就是最可怕的「陷阱」,一番問答下來,往往令自信十足的「初生之犢」們鎩羽而歸。「不要氣餒,這是導師的『見面禮』,不是導師的真面目……」,「牛津手冊」如此「撫慰」新生。

過關斬將,傲氣十足
導師肩負著學生們的學識與生活,是各學院吸引學子的有利招牌。由於每年六月大考時,各學院要為學生做好萬全準備(兼指頭腦和儀容),將他們送入大學設置的統一考場,事後還有成績排名。因此各學院為了爭取榮譽,總是千方百計挖角求賢,網羅素負盛名、勤管嚴教的導師以壯大陣容。
牛津人「傲」,也是因為人人都曾過關斬將,身經百戰。在高中會考(A-Level)中成績達一定程度者,才有資格向大學入學許可諮詢中心(UCCA)申請進大學就讀。而全英四十六所大學中,牛津、劍橋偏「與眾不同」——不同的申請表格、特設的入學測驗(考試及面談);「學部」錄取不算,還必須同時拿到某個「學院」的入學許可……。要成為「牛、劍」人,絕非易事。英國大學採「菁英主義」,就學率低,大約只佔十八至廿一歲年齡層的百分之十;而「牛、劍」人更是「菁英中的菁英」,氣燄之高,有他的道理。
正因為「傲」,競爭激烈也就不在話下。
出國前曾在大學中授課的蔡明琪指出,英國大學一年三學期,一學期僅有八週,「但可不是八週讀一本教科書」,他說,牛津授課,是以「專題」為中心,例如這週探討「存在主義的盲點」,教授蜻蜓點水式地挑出指定書中某章節的某些論點,至於正辯、反辯、旁徵博引,則請自己參閱教授開具的書單!
於是平日舞會、酒吧,好不逍遙,但到學期末「報告危機」(essay crisis)時刻,通宵達旦不足為奇,苦的倒是心理壓力太大,有時間睡覺也睡不著,同學間「安眠藥換著吃」,也就顧不了傷神傷身了!

腦力的煉獄、天才的天堂
大學部如此,但在以「獨立研究」、攻讀「研修學位」(by research degree)為主的研究所中,又是另一番氣氛、另一種「危機」。
「所謂『研修學位』(博士只有此種學位)和『研讀學位』(by course)不同,就是不必上課、沒有考試,只須定時(或不定時)找指導教授談一談,其他的則完全以一篇畢業論文『定生死』」,攻讀漢學博士的葉其忠指出。
不上課不考試,連小組討論也不必,那豈不是好「混」?「門外漢」或許不免詫異;唯有當事人,才知道個中艱辛。
「獨立研究固然沒有外來壓力,但自我要求往往更嚴格。一切理論創見,都得從自己內心深思反芻後,一點一滴錘鍊出來」,李惠凡說。而指導教授雖都是名重士林的大學者,但為了避免給學生「錯誤的引導」,因此在提出意見時也非常「保留」,一切尊重學生。在這種情況下,「內心沒有東西」的人,若想光憑東撿西湊,是很難通過所謂「腦力煉獄」試煉的。
「維持心情的『定』、『靜』,是先決條件」,黃克武指出。但是談何容易?!「我到底是不是做學問的材料?」「討論這些空泛理論究竟有什麼意義?」「還要拖多久才能拿到學位?……」一連串的自我質疑,常令早生華髮、心力交瘁的研究生們夜半驚醒。
「牛津是為啟發天才而存在,不是為教育庸才作無謂的努力」,這是牛津研究生頗為認同的信念。
對教育頗有興趣,也常和各國留學生討論的李惠凡則提出他的看法:「美國教育,基本上是『機器改良』式:考啊、磨啊,總要把你修正得頭角完美。但牛津則採『發酵』式:你是塊酵母的料,牛津就負責給你最好的環境,讓你自己滋長發酵;你若本身缺乏酵素,那也怨不得別人幫不上忙。」
牛津也逐漸在變
被批評「象牙塔內的冥思」也好、「與社會脫節」也好,牛津對學理有著近乎崇拜式的執著。「早在兩百多年前,牛津就以社會經濟理論著稱,但直到五年前,牛津才正式開始企管課程。原因無他:經濟是一門深奧的學理,而企管只是『術』,不值得識者一顧」,楊瑩舉例說。
因此,儘管首相佘契爾夫人上台後,以「實利」為著眼點,將教育重心轉向標榜「建教合作」、以企業為導向的新興大學及多元技術學院,但牛津人毫不擔心。「層次不一樣」,他們會告訴你:「設備再好、經驗再多,也比不上一張紙、一枝筆,和一個會思考的腦袋!」
話說回來,牛津終究不斷在「變」。
精緻古老的建築中,學者們正致力於前衛思想、尖端科技,以契合時代脈動;華服革履、顧盼生姿的貴族子弟,夾雜在一大群牛仔粗布的平民學生中,已經顯得突兀;最後一個「僧侶學院」——Oriel,也已於去年招收女生;而近幾年,儘管諸多反對聲浪,「麥當勞」還是在牛津城中心佔據了一席之地……
傳統與現代、貴族與平民、理想與功利,牛津的面貌繁複多姿。讀書、讀史、讀人、讀事,牛津一遊,都啟人深思。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