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七歲的蔡瑞月與八十五歲的老師石井綠在台相會,細說一甲子前的故事。(邱瑞金)
假如我是一隻海燕,永遠也不會害怕,也不會憂愁,我愛在狂風雨中翱翔,剪破一個巨浪又一個巨浪,而且唱著歌兒,用低音播唱愛情的小調。但我的進行曲,世間也沒有那樣昂揚。風靜了,浪平了,我在晴朗的高空,細細的玩賞,形形色色的大地。──「假如我是一隻海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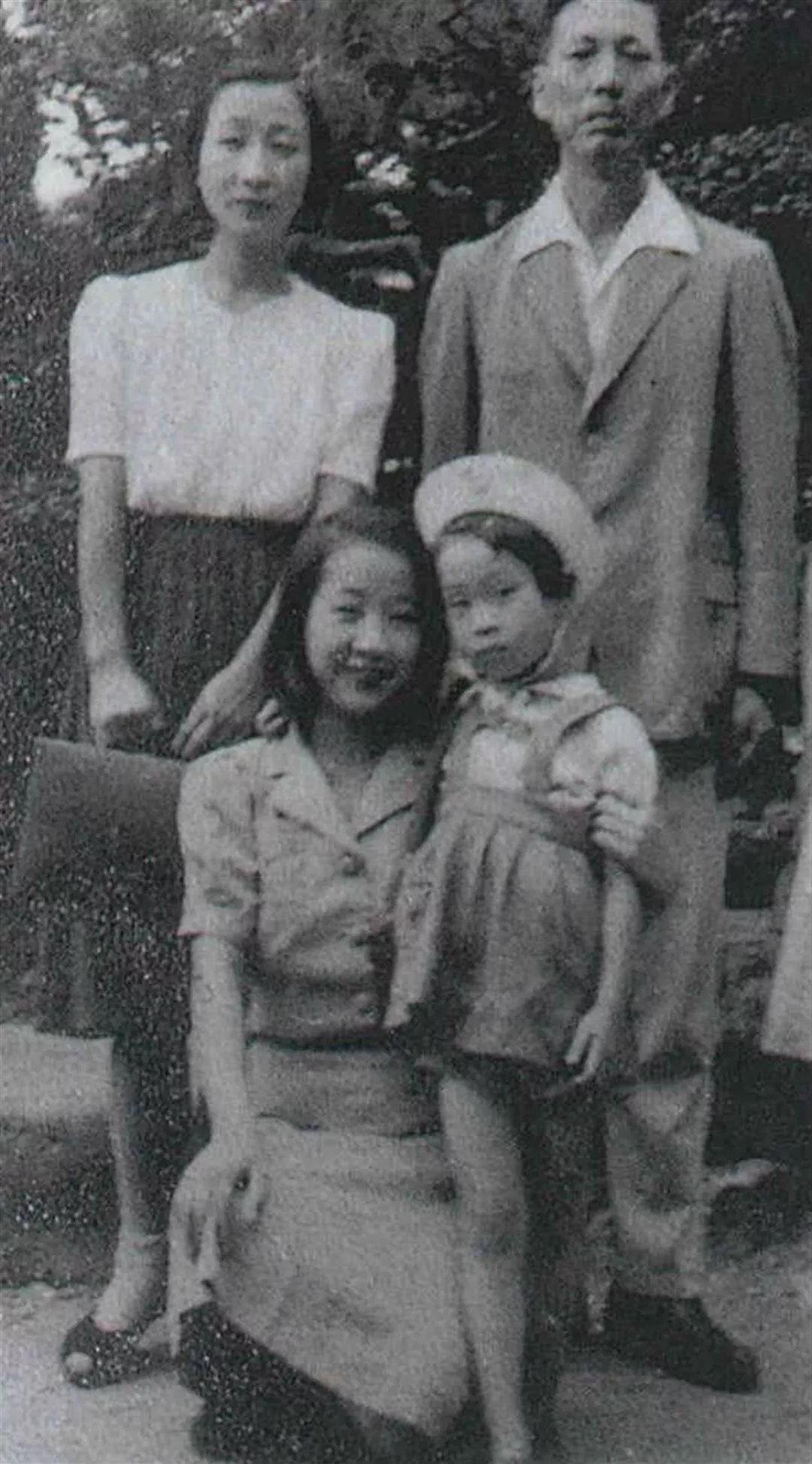
十六歲赴日學舞的蔡瑞月(前蹲者)與老師石井綠(左)及其家人合影。(蔡瑞月提供)(蔡瑞月提供)
將近五十年前,台灣現代舞之母蔡瑞月以其夫婿雷石榆的詩作,在舞台上發表創作新舞。舞台下的蔡瑞月也如詩中的海燕一般勇敢,歷經新婚夫婿被逐出境,自己被囚兩年後,獨力扶養獨子長大,同時她的舞鞋不曾擱置。在那個處處受制的環境裡,蔡瑞月以一個女性的生命力以及對舞蹈的摯愛,為台灣現代舞開啟一扇又一扇的門窗。

去國多年,在兒子雷大鵬(右二)與媳婦蕭渥廷(左三)的相伴下,蔡瑞月開心的參加學生們為她舉辦的慶生會。
一月底,日本國寶級舞蹈家石井綠抵台,與她十多年不見的學生蔡瑞月在飯店緊緊相擁,隨即在已有半世紀歷史的中華舞蹈社舉行記者會。八十五歲的石井綠與七十七歲的蔡瑞月話匣子一打開,回憶源源不絕地流洩出來。在課桌下偷偷練習舞步
石井綠表示:「數十年的舞蹈生涯讓我培養出了兩顆鑽石,就是我的女兒和蔡瑞月。」會後兩位頭髮花白的老祖母在舞蹈社裡即興式地翩翩起舞,時光彷彿又回到六十年前……
西元一九二一年,台南一位蔡姓旅館老闆在兩個兒子之後,喜獲掌上明珠,取名為瑞月。這個小瑞月在四、五歲的時候,經常一人在家跟著日本童謠「桃太郎」又唱又跳,一下子扮演桃太郎,一下子扮演猴子,一下子又演火雞。小學時光,她最喜歡體操課裡的舞蹈課程,每逢那一天,她就在課桌下偷偷地練習上週教過的舞步,而無法專心聽課。
畢業後,小瑞月考上台南州立台南第二高校(今天的台南女中),她依然把握每一個可以跳舞的機會,連早上的體操課,她都盡情伸展,一如一隻展翅的燕子。體操老師發現了蔡瑞月的舞蹈天份,開始安排她加入每年校慶的舞蹈表演。即將畢業的蔡瑞月也開始蒐集日本舞蹈學校的資料,決心畢業後就要遠渡重洋去日本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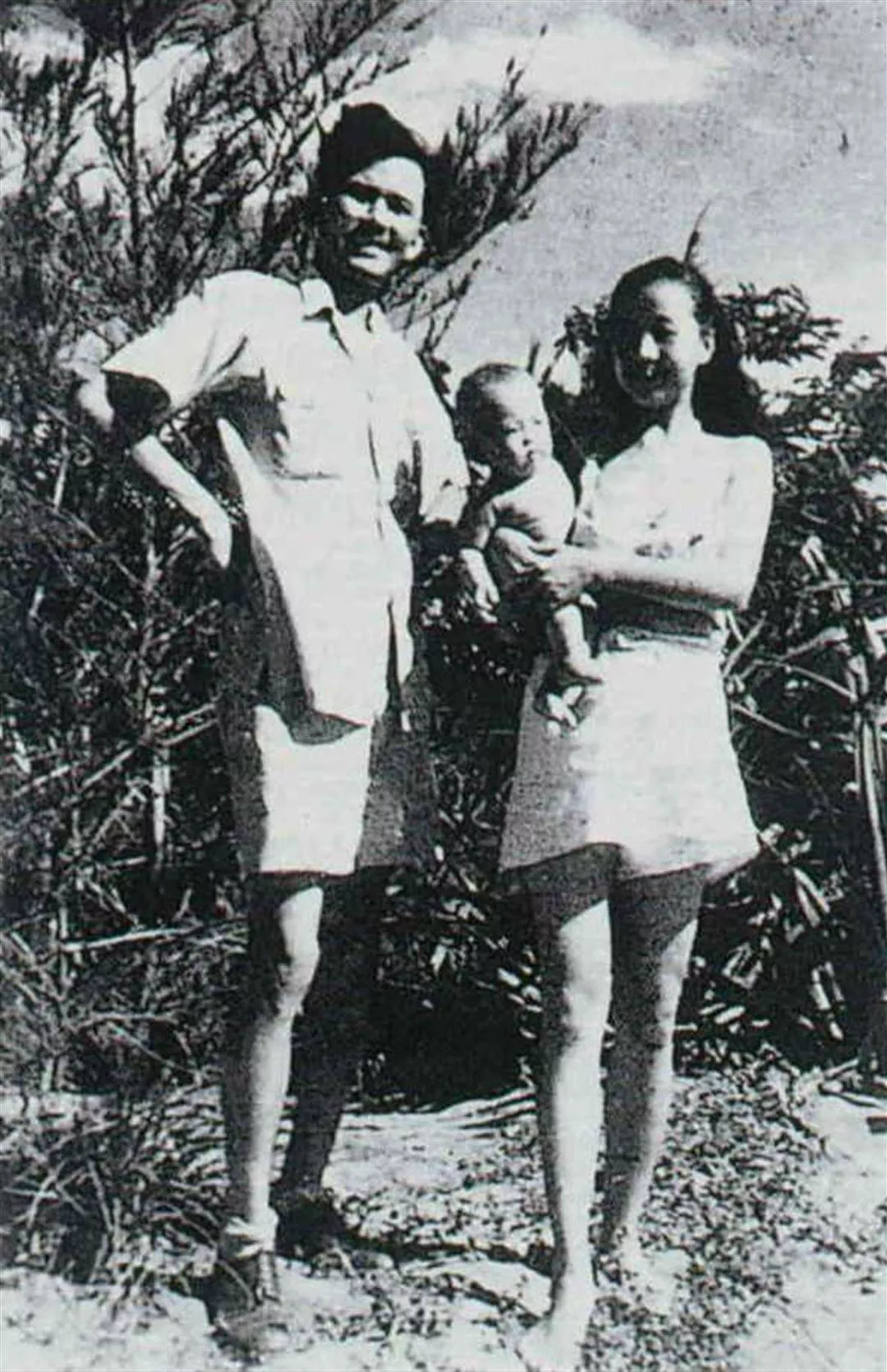
右)彌足珍貴的一張合照,訴說著蔡瑞月與雷石榆短短年餘的恩愛姻緣,留下無盡的感嘆與說不完的故事。(蔡瑞月提供)(蔡瑞月提供)
那個年代,舞蹈不僅沒有被當成一種藝術,可以說人們對舞蹈的了解幾乎等於零,同學們以為蔡瑞月要去參加日本著名的「寶塚」舞團,而自幼與蔡瑞月相識的二嫂盧錫金聽說她去學跳舞了,心中還難過地嘆息:「怎麼這麼文靜乖巧的女孩子,竟然跑去當舞女?」燕子去又回
然而,才十六歲的蔡瑞月,在體育老師的大力幫忙,及賭氣離家跑到鄉下教書的「決志」下,終於使對她疼愛有加的父親讓步。在高雄買了一張三等艙船票,前往當時東方的現代舞之都──東京,並進入當年日本最重要的現代舞中心──石井漠舞踊專科學院。
石井漠在日本享有「日本現代舞之父」稱譽,是日本第一批學習芭蕾舞及現代舞的舞者。隨後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重要的舞團紛紛停擺,然而蔡瑞月卻透過老師,接續了西方的現代舞技巧及理念,並隨著石井漠及石井綠舞團到緬甸、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演出,這一千多場的演出除了增加經驗,更使蔡瑞月的視野大開,廣闊地吸收了各國的民族舞蹈風格。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結束五十年殖民歲月,隔年二十五歲的蔡瑞月搭上貨船實現了她十六歲前來日本學舞時的許諾──一定要回到台灣開拓故鄉的現代舞空間。

在台灣舞蹈界還是一片荒蕪的年代,中華舞蹈社是國外藝術團體必到之處。(方淑華提供)(方淑華提供)
在這一艘載滿留日學生的船上,清涼的海風遠遠送來故鄉記憶,每天清晨五點多,蔡瑞月就登上甲板,迎著海風忘我的練舞,有的大學生笑說她是一個瘋子,也有熱愛音樂、美術的大學生協助蔡瑞月,為她伴奏、找樂譜。一群人就在歸鄉的路上,以台灣作曲家蔡培火的《咱愛咱的台灣》為歸鄉學子跳出台灣農村的景致,也跳出離鄉學子們思鄉情懷。這一群意氣風發的年輕學子正要回到故鄉開拓生命的春天。 當文學碰上舞蹈
從基隆港上岸,回到台南老家,蔡瑞月立刻開設了台灣第一個舞蹈研究社「蔡瑞月舞踊藝術研究社」。穿著台灣第一雙芭蕾舞硬鞋跳出「垂死的天鵝」、「新的陽傘」,並以大鼓和鈸鐃等打擊樂器伴奏,在隆隆樂聲中跳出台灣戰後,百姓團結共苦重建一切的現代舞「建設舞」。
從離開台灣到回到台灣,故鄉的風氣依然保守,當蔡瑞月開始排練男女雙人舞時,學生紛紛勸她打消念頭,大哥甚至對她說,要是跳了男女雙人舞,就要準備這一輩子嫁不出去了。果然排練過程中,不僅舞蹈教室的房東收回了出租場地,甚至有人認為這樣的舞蹈有礙風化。然而蔡瑞月這樣一個生於古都台南的文靜女子,卻無視於社會的雜音,依然堅持自己的理念,第二年還北上台北,在中山堂舉辦「蔡瑞月創作舞踊第一屆發表會」,破天荒地由首屈一指的省交響樂團為她伴奏,轟動當時的藝術圈,也讓更多沒見過舞蹈表演的觀眾大開眼界。

不論是各國民族舞蹈、現代芭蕾或是中國民族舞蹈,任何素材在蔡瑞月心中都是創作的絕妙靈感,任何舞蹈形式都能叫蔡瑞月忘我的起舞。(蔡瑞月提供)(蔡瑞月提供)
年過六旬,當時就讀新竹女中的方淑華記得,那個時候,學校裡沒有任何舞蹈科系,社會上沒有舞蹈的電影或書籍,中山堂的表演也以音樂會居多,要看到一場舞蹈發表會真是千載難逢。她無意中看到了蔡瑞月的創作芭蕾舞,立刻給迷住了,於是週六日就住在台北蔡瑞月家中學舞,成為蔡瑞月在台北的第一個學生。一錶定終生
在與省交搭配的的日子裡,蔡瑞月結識了省交編審雷石榆。這位留日的廣東台山人,能詩能畫。留日期間出版過日文詩集,並與詩人覃子豪、紀弦在日本共組詩社。光復後,雷石榆是第一批來到台灣的文藝界人士,為台灣大學延聘為文學教授。
對蔡瑞月而言,這位雷先生日語、國語皆流利,雖然已享盛名,卻熱心地為尚不會講國語的蔡瑞月翻譯,並經常以腳踏車載著她與其他藝文人士或記者們結識。蔡瑞月發覺自己越來越依賴雷石榆,當台北的演出結束即將移往台中、雷石榆不需隨團之際,她突覺若有所失,情緒低落。

不論是各國民族舞蹈、現代芭蕾或是中國民族舞蹈,任何素材在蔡瑞月心中都是創作的絕妙靈感,任何舞蹈形式都能叫蔡瑞月忘我的起舞。(蔡瑞月提供)(蔡瑞月提供)
沒想到就在前往台中的前一晚,雷石榆送蔡瑞月到二哥家巷口時,摘下了手腕上的舊錶向她求婚,蔡瑞月默默地收下了這支定情的手錶,這一對熱愛藝術的才子佳人在相識三個多月後,步上紅毯。對蔡瑞月而言,不論是愛情婚姻或是舞蹈生涯都綻開了最美麗的花朵。冬天來了
婚後的蔡瑞月新舞創作不斷,在懷著八個月身孕的時候依然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舞台下的觀眾竟看不出來,這個胎兒日後自然註定成為舞蹈家。就在兒子雷大鵬出生的同年,蔡瑞月以原住民為主題,編出大型舞劇「水社懷古」。
蔡瑞月的二嫂盧錫金記得籌備舞劇時,當時台幣大貶,許多布莊藏起較好的布料,蔡瑞月走遍了布莊買不到所需布料,急得在馬路上流下淚來。最後水社懷古的舞衣是由蔡瑞月的嫁妝布和粗布拼湊而成,舞衣則由二嫂依照蔡瑞月找到的資料,一針一線縫製出來。
然而這樣詩作、舞作與稚子笑聲交融的美好生活卻短暫得令人扼腕。蔡瑞月新婚一年多的淡淡春天,當一家三口買好了船票即將動身前往香港教舞的前一晚,豐盛的餞別宴正在進行,有個人說台大校長要找雷石榆,雷石榆跟著出去,卻從此再沒踏進過家門。

不論是各國民族舞蹈、現代芭蕾或是中國民族舞蹈,任何素材在蔡瑞月心中都是創作的絕妙靈感,任何舞蹈形式都能叫蔡瑞月忘我的起舞。(蔡瑞月提供)(蔡瑞月提供)
焦急而驚慌的蔡瑞月幾經打聽,才知道雷石榆因政治迫害輾轉被關在基隆,且即將驅逐出境。蔡瑞月抱著才幾個月大的大鵬天天輾轉換車到基隆探監。奔波了四、五天,蔡瑞月擔心大鵬累了,於是一個人前去基隆,那知雷石榆正被押解上船。蔡瑞月追上前去,央求跟著丈夫一同被流放,卻隨即想起了──大鵬不在身邊,於是停下了腳步,眼睜睜望著丈夫被驅逐出境。風雪不止
原本蔡瑞月心想著,等丈夫到廣州後,取得聯絡,她便要辭別父親,再辦一場告別演出,告別台灣隔海尋夫去。那知辦了手續,才發現自己被限制出境,她這才知道事態嚴重,恐怕再也見不到丈夫了。那一陣子,蔡瑞月經常一邊走路一邊掉淚,所幸在舞蹈的支持下,使得她一個舊時代女性在生活及精神上仍有所依靠。
然而噩運並未結束,在雷石榆被驅逐出境幾個月後,蔡瑞月也遭逮捕入獄兩年。然而即使身陷囚牢,外柔內剛的蔡瑞月依然靠著監獄裡的柱子壓腿拉筋,保持柔軟度,甚至還教獄中的牢友跳舞。媳婦蕭渥廷說:「每當我遭到挫折時,只要想到婆婆在那樣的打擊下,竟然還繼續練舞,令我深刻體會到,原來藝術家之所以被尊重,是你可以拘禁我的身體,但是你永遠抓不到我的靈魂。」
出獄當天,蔡瑞月第一件事是趕往台南大哥家看大鵬,而大哥卻在當晚因蔡瑞月而被抓走。「家人連續遭到逮捕之後,我的腿只要往下壓,膝蓋就會不停的發抖。」

(右)中山北路二段的小巷裡,這塊小小設計木牌後,就是藝術家們曾經群起保衛的中華舞蹈社。
往後多年的日子,蔡瑞月在監視下,每個月得到駐地警察局報到,並繳交生活報告書。面對許多國外演出機會,她的作品和學生可以去,就是她不能去。「對我們而言,當時的台灣就像一個大的集中營,很不自由,」母親入獄時才一歲多的雷大鵬,成長的記憶有太多的禁忌。風與葉子的起舞
出獄後,蔡瑞月將舞踊藝術研究所改名為中華舞蹈社,搬到位於中山北路巷子內的現址,游好彥、曹金鈴、蔡光代、蕭靜文、李維、崔蓉蓉等現代舞蹈家,都曾推開那一扇紅門,開始他們舞蹈的啟蒙。
現任台北愛樂電台董事長的胡渝生是蔡瑞月兒童班的學生,跟著蔡瑞月學舞十七、八年。「跟蔡老師上課很享受,像在遊戲一般。蔡老師經常要我們一群小朋友想像自己是一片葉子,而她則是風,每當風吹起來,我們就隨意的跳躍、翻滾、伸展自己的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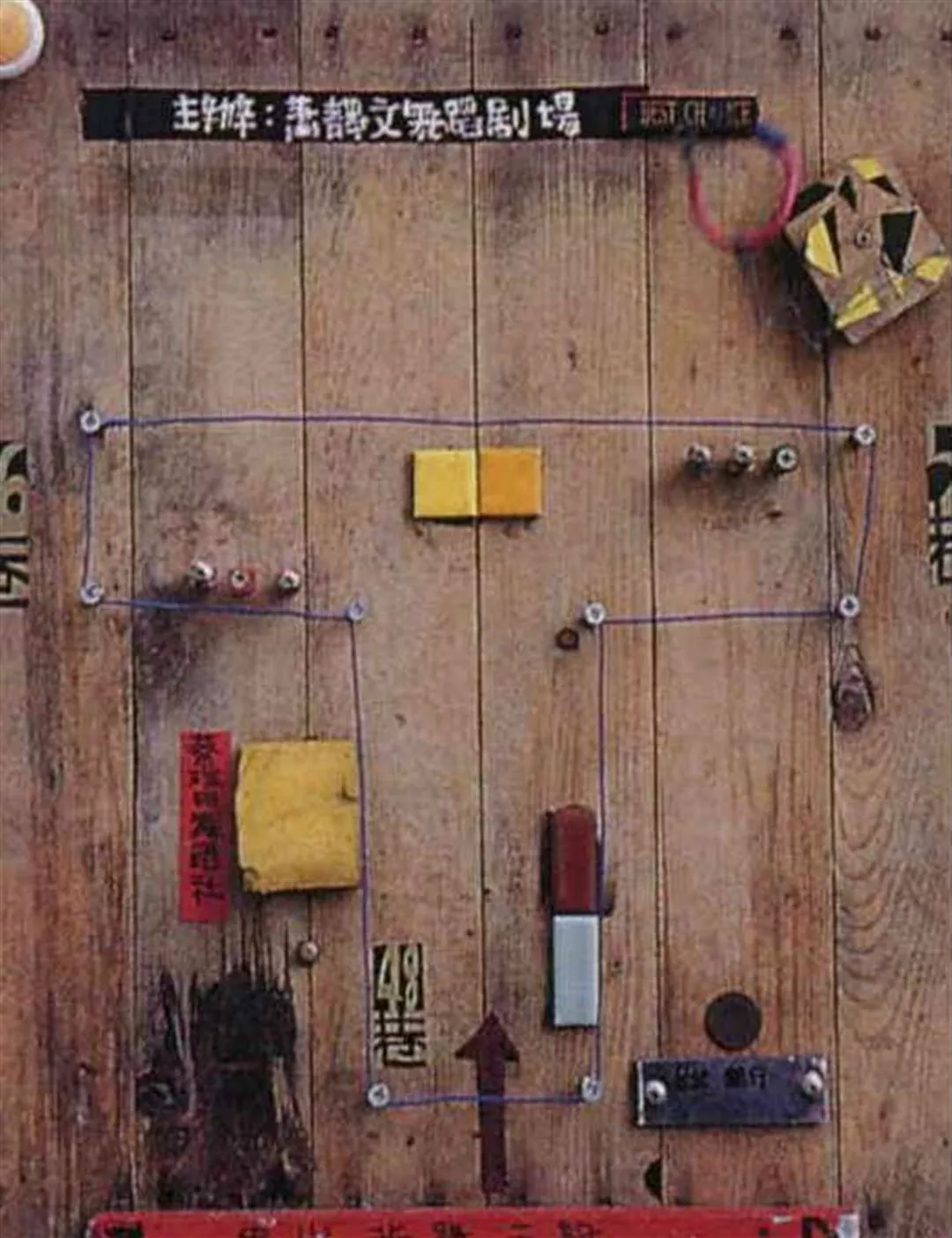
頭髮也近花白的學生們陪著老師回到中華舞蹈社。這塊地板上,留有眾多舞蹈家辛勤練舞的汗水,也記錄著台灣舞蹈界的歷史。(邱瑞金)
藝術之家
今天看起來小小的中華舞蹈社,在當時是台灣最大的舞蹈中心,高峰時期不僅有三百多個學生,全台還有八個分校。經常蔡瑞月就坐著火車到各個分校去教課,一個人在火車上或是火車站裡休息。
也因此,當時的國外舞蹈家來到台灣演出,大多不會錯過中華舞蹈社。諸如美國的現代舞蹈家金麗娜就曾在此短期授課,日本舞蹈家加藤嘉一、韓國舞蹈家趙勇子都在此出現過。而國內的藝術家也喜歡聚在中華舞蹈社,攝影大師郎靜山、畫家楊三郎、顏水龍,都為蔡瑞月留下許多珍貴照片及畫作。舞蹈社在當時是一個藝術的理想國,年輕人在此充分享受著創作的樂趣。
創作一如生活精采,經蔡瑞月編排搬上舞台的大型舞劇或自創舞碼有數十部,在資訊缺乏的年代,有時她根據國外的演出劇照排演,有時自己按照故事大綱編舞,有一次為了「垂死的天鵝」,她的學生看了芭蕾舞星瑪歌芳婷主演的電影《火鳥》舞劇近百遍,好為蔡瑞月記下每一個舞姿。大型的芭蕾經典舞劇《天鵝湖》、《吉賽兒》、《羅密歐與茱莉葉》都經由蔡瑞月首次搬上台灣的舞台。
民國四十年代,政府大力提倡「民族舞蹈」,為了爭取演出機會,蔡瑞月也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民族舞蹈。有一次,學生李清漢告訴蔡瑞月,他的同學姚浩家鄉有人用杯子嗑嗑嗑地跳舞,蔡瑞月聽了大感興趣,找來姚浩哼出音樂,並延請中廣樂團錄製曲子。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苗女弄杯」,就是這麼來的。

一回到舞蹈社,學生們紛紛隨著音樂伸展肢體,蔡瑞月也與最頑皮的學生、六○年代的歌舞紅星林沖跳起雙人舞。(邱瑞金)
為了吸收中國傳統舞蹈的相關材料,她特別向平劇界的蘇盛軾、哈元章學習彩帶、水袖、槍劍身段,像是劍舞、盾舞、翎舞等民族舞蹈,也都是蔡瑞月自平劇中吸取靈感獨立發展出來的。「什麼素材一到蔡老師手上,就變成很好的舞蹈,」李清漢表示。飛離心愛的傷心地
民國五十年代後期,大專院校開始出現舞蹈科系,學舞的孩子大量流向學校,開拓台灣舞蹈界近二十多年的私人舞蹈社飽受衝擊。
民國六十一年,雷石榆在大陸文革時一同受難的音樂家好友馬思聰在美國投奔自由。馬思聰聯絡上蔡瑞月,並且慨然表示要為蔡瑞月創作舞曲。
對年近六十的蔡瑞月而言,這一部取材聊齋故事《晚霞》的芭蕾舞劇將可以為她的舞蹈生涯創下另一個高峰。然而,在馬思聰向台灣一處公家單位申請補助之後,原本是主角的中華舞蹈主導權不斷被削減,最後更以「民間團體不足以勝任這樣大型的演出」,將舞劇轉給藝專舞蹈科。
再一次的政治干擾藝術,令蔡瑞月母子徹底感到失望。於是民國七十二年,蔡瑞月決定隨曾參加澳洲現代舞團的兒子雷大鵬移居澳洲。
早期白色恐怖的影響對這對母子實在太重了,親人都希望蔡瑞月能擺脫陰影過著輕鬆的日子。因此,儘管妻子蕭渥廷與雷大鵬才新婚一年,她還是鼓勵丈夫留在澳洲陪婆婆,而她則留在台北管理中華舞蹈社。
對於蔡瑞月而言,兒子還在襁褓中就失去了父親,兒子在最需要母親懷抱的時候,她又在牢獄之中。於是往後的日子,她幾乎都形影不離的帶著大鵬。

旅澳的日子,蔡瑞月醉心於油畫與陶板的創作,創作主題依然是她一生的最愛——舞蹈。(邱瑞金)
對雷大鵬而言,父親的印象僅靠著一些殘留下來的著作,及一件友人輾轉送來的咖啡色夾克。平日生活裡,母親同時是父親。他特別護衛母親,但也抗拒追求母親的愛慕者,到了自己結婚,想到母親一生的孤寂,他也將母親放在妻子之前。兩代三口,都為體諒彼此,隱忍自己的幸福。相見爭如不見?
在澳洲的期間,蔡瑞月也在兒子、媳婦的陪伴下,到大陸與四十年不見的丈夫相會。
當一家人在大陸保定車站見面時,他們兩人皆已白髮蒼蒼。「我覺得,在他們的人生旅途中,彷佛有一片很大的陷落,連不起來。剛開始,兩人靜靜站著,後來是蔡老師上前去擁抱雷爸爸,一家人都講不出話來,」蕭渥廷敘述當時會面的狀況。
回到雷家,又是一個大家都辛苦的局面,因為雷石榆已經再婚。三方面都有複雜的心情,但三方也都儘量地包容彼此。在台灣遭到驅逐出境的雷石榆,在大陸文革時又遭打斷肋骨。雷石榆不禁感嘆地說:「我們這一代,要當中國人,卻兩邊不是人。」
在澳洲的日子,蔡瑞月母子依舊開設舞蹈教室,教導一些華裔子弟跳舞。之後他們又移居到澳洲的渡假勝地布里斯班,母子倆開始醉心於繪畫,藉著陶板、油畫,蔡瑞月描繪出一個個美妙的舞姿。

剪破一個又一個巨浪,創作一齣又一齣的大型舞劇,現在的蔡瑞月希望靜靜地回顧自己這一生的故事。(邱瑞金)
過去的大半輩子,蔡瑞月忙於教學、表演,以及與現實社會對抗,如今她希望能好好地回顧自己過去的每一個片段。閒暇之餘,雷大鵬會拿出錄音機與筆記本,細細地記錄下蔡瑞月生命的點點滴滴。日落黃昏時候,他們也會在沙灘上散步,對著南太平洋的落日隨興地起舞。昔日的海燕,依然嚮往自由自在的飛舞。誰是蔡瑞月?
雷大鵬陪伴蔡瑞月在澳洲隨興度日,位於中山北路的中華舞蹈社則由媳婦蕭渥廷帶著兩個孩子住著,並持續經營。對於年輕的舞者或學者,由於蔡瑞月去國近十五年,而她的學生從事教育的又不多,這樣一塊培育眾多舞者的園地也日漸被遺忘。
四年前,因為捷運工程,只擁有地上房屋權的中華舞蹈社面臨了被拆遷的危機。蕭渥廷急忙召集蔡瑞月的學生向藝文界發出求救聲,舉辦了「向蔡瑞月致敬」活動。牆上掛著蔡瑞月過去的照片、演出節目單、當時珍貴的服裝、道具。而蔡瑞月夫婦的好友劇作家魏子雲,深富感情地朗誦著雷石榆為蔡瑞月所寫的詩作《假如我是一隻海燕》,台灣光復半世紀來的舞蹈歷史就在木造的中華舞蹈社裡流轉。然而藝文界的共襄盛舉,大多只是惋惜、追憶,或表示希望留有舞蹈教室的一塊地板。
於是,蕭渥廷決定以一種「高能量甚至向生命耐力挑戰」的活動,來展現他們對保存中華舞蹈社的決心。很多人可能都還記得,八十三年九月席斯颱風前夕,風雨交加,然而台灣的藝術團體幾乎全擠到中山北路二段台北銀行的巷子裡,一波又一波的觀眾感染了藝術家們的熱力,隨著巷道裡、舞蹈教室內接力賽地二十四小時表演的舞者情緒沸騰,而蕭渥廷則與兩位舞者以吊車掛在十五層樓左右的高度上一整夜。搶救活動終於獲得當時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水扁的許諾,當選後立即留下了中華舞蹈社。
活動的過程,蔡瑞月沒有回台,如今她雖獲教育部頒的薪傳獎,市政府卻要拆除充滿她一生歲月的老房子,她怎麼回得來?永遠的海燕
然而,終究她還是回來了,今年二月,二十多位蔡瑞月的學生齊聚在圓山飯店,為七十七歲的老師慶生。這群學生早期的已經年近七十,晚期的學生也在五十上下。至今依然在教舞的祖母級學生方淑華表示,在她們生長的年代,父母給她們幼年的快樂,丈夫提供她們中年的幸福,而蔡老師使她們的少女時代充滿光彩、活力。
慶生由中午持續到黃昏,一行人興致勃勃地回到老舊的中華舞蹈社。老舊的房子樑柱已經被白蟻蛀得差不多了,每逢下雨,補不勝補的瓦頂滴滴答答四處漏水,學生們經常以音樂伴著水桶接水聲來練舞。然而,它又是那樣一個美麗的地方,空氣中瀰漫著昨日的心情、故事,落地鏡子裡,依稀可見一代代舞者伸展肢體的盛況,地板上留著舞者的汗水,讓人進入舞蹈社就全身放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釋放感。
自然地,有人放起了音樂,頭髮花白的學生們紛紛脫下鞋子,在這補了又補的木頭地板上隨意起舞。一向最活潑的學生林沖擁抱老師跳起雙人舞,並做出民國四十二年「月光曲」表演節目單的封面舞姿。
真正的勇者
一向沈默寡言的蕭渥廷在一旁靜靜地處理事物,身為蔡瑞月的學生,又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同樣熱愛舞蹈又身為女性,她對蔡瑞月的一生感觸很深。「她是那樣勇敢,每每在她的時代跨出新的腳步,而且她的勇敢不是一時的,而是一輩子的堅持。我希望能重建老師的舞蹈作品記錄,因為蔡老師對舞蹈熱愛的精神、一生所煥發的生命光彩,正是現代舞蹈界的一面鏡子。」
在這四週大樓夾雜的中山北路小巷裡,蔡瑞月在生命的困頓中,開展了台灣現代舞的第一頁,而蕭渥廷也以對舞蹈的熱愛,承擔起台灣舞蹈史的保存。對舞蹈相許一生的兩代女性以無比的韌力,跳出了令人驚艷的海燕之歌。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